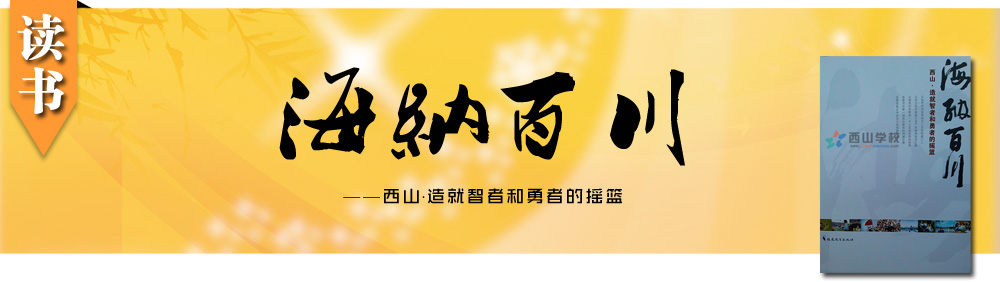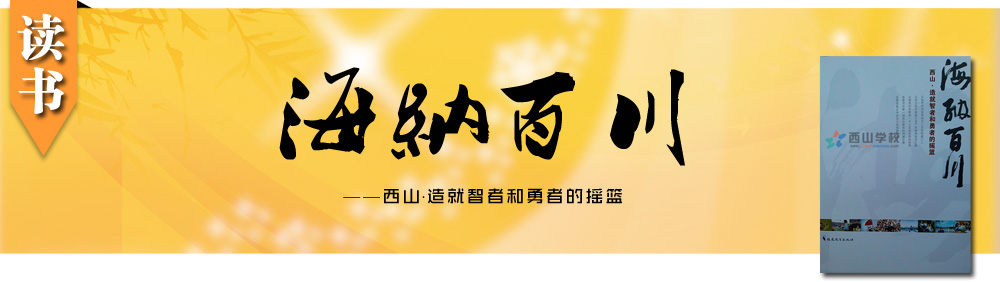办武术学校说千道万得凸显一个“武”字,张文彬让人在营房的操场中间砌了一堵墙,墙上描上了一个巨大的“武”字,让进入西山武校的教练和学生天天看着、拜着。那时候,张文彬严格要求教练们,要一个月内教会学生散打中直拳、摆拳、勾拳、边腿、登腿、踹腿等一系列动作;二十天内要教会学生剑术中的刺剑、劈剑、点剑、崩剑、截剑、挂剑、拌剑、斩剑等一系列要领;二十天内要教会学生刀术中的扎刀、缠头刀、裹脑刀、劈刀、截刀、斩刀、云刀、撩刀等一系列技术;半个月内要教会学生枪术中拦、拿、扎枪、左右舞花枪、挑把、绞枪等一系列功夫;半个月内要教会学生棍术中劈棍、抡棍、扫棍、戳棍、崩棍、撩棍、左右舞花棍等要点。对不吃苦,不出力的学生要严加管教。他发誓要把西山武术学校的武术训练抓上去,把名声拼出来。
超强训练在西山武校开始了。
拉练式的长跑,左跑甘厝口,跑镜洋镇;右跑墩头村,跑东张镇,或是来回跑趟南少林寺……
学生中,来自漳州漳浦的杨全明、广东海陆丰的温泽瑞、闽东寿宁的吴大生和康志勤等等都十分出色出众。
1995年福建省第九届运动会在三明市举行,西山武校首次组建代表队参加,康志勤在大赛中获得武术散打52公斤级第四名。
西山在大赛中不曾夺魁,但毕竟打出了旗号,是零的突破,这也创造了西山武校在武术赛事中的历史性记录。
参加全省赛事后,张文彬更是狠下决心,要使西山武校的武术水平更上一层楼。于是就开展了西山武校“武状元”争夺赛。争夺赛以淘汰赛的办法举行,逐个按级别打,全校参加,当作考试。
争夺赛的结果是,来自漳州漳浦的杨全明获得了“武状元”称号。西山武校奖给杨全明两个塑料制作的奖杯,奖杯用红色缎带扎着,显得格外的喜庆。杨全明把这对奖杯捧回家后,他的老母亲把儿子这两个奖杯摆放在列祖列宗的供桌上,告慰杨家列祖列宗说:他们的后代当上“武状元”了,不但获奖的子孙高兴,就连供桌上的杨家祖先也会欣慰不已的。另外,作为奖品的两本笔记本,杨全明也舍不得用,深深地锁在箱子里。
在高强训练之下,西山武校学生的武术水平在整体上打了一个翻身仗。
当年部队的旧营房四面各个房间都住满了教练、老师和学生,营房中间一隔几块,练功习武的,练臂力的,练腿功的,练跑步的,打球的,再找不到空地了,即便是场地中间的那棵大榕树,也都充分利用,大冬瓜似的悬挂着长长短短的沙包,供学生们练拳击。
一校之长的张文彬眼看着活动空间日益缩小,不得不把视野投向营房外围。他三番五次地去考察,发现营房外左边方向,可利用的空间有限,正前方和右边方向的可利用空间却是很大的。他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着,哪一天手头的经费较宽裕了,就一定要向外扩展。但如今创校之始,一分钱恨不能掰作两半来用,哪有买地建房的钱呢?去借钱?茫茫人海,谁能几十万甚至百万地把闲钱借给你?去贷款,银行放出贷款,是要以自己的财产作抵押的。而自己这武校,除了向部队租用的这一圈营房外,别无值钱的物件。总不能把自己和教练们拿去充作抵押吧。再就是向政府求援?这就更是此路不通了,这武校是林秉国和自己一人出钱一人出力办起来的,纯属个人行为。不仅别想让政府援助,政府不来发难,就谢天谢地了。尽管自己也是与公立学校一样,天天都在为国家、为社会培养人才,但待遇和处境就硬是不一样,没地方讲理的。怎么办?这条路不通,就只有自力更生了,发奋图强的路才是自己广达通畅之路。
无数次了,张文彬用自己的脚步反反复复“丈量”了周边的山丘、草地,以及乱石滩。他先是紧紧盯着营房右方向的两口废弃的鱼塘,练武的人不能没有一处擂台。这擂台在营房内是建不了的,只能把这两口废弃的鱼塘填起来,充作擂台用地。主意打定了,他就向教练、老师和全体同学发出号召。从此,凡有空闲,全体西山人都会向那两口废弃鱼塘里填土投石。愚公可以移山,西山人可以填塘,没有不成功的。不久,西山武术学校新落成的大比武擂台,就在旧鱼塘地址上矗立了起来,从此,西山人有了一个比武打擂的好去处。
擂台落成那天,校长张文彬指着营房大门正对面墙壁上书写的警句,对着他的学生们说:“记住了,我们练武的人,一定要弘扬武术,苦练武功,讲求武德,争雄武校……”
学生多了,班级也多了,家长的要求就更多了。西山武校为顺应形势变化,也顺应家长的要求,不再让走进西山的学生单一的学武练武。把没能很好学文化的,尚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们,集中成4个班级,分别由陈美桥、杨厚宝和绰号叫“四眼镜”以及他的未婚妻带班教学。陈美桥等4位文化课教师,把自己所负责班级里的语文、数学主课和其它副课统统包干。
这就是西山文武学校的雏形。
尽管开设了4个班级的文化课,但“武术”是西山的主体。校长张文彬曾多次在全校教练和学生中强调:“西山武术学校,就是要学武,要毫不动摇地突出“武术”这二个字,没有武术,就没有西山武校。
以武术为主体教学内容的西山武术学校,里里外外的大事、小事都由武术教练说了算。 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。
那时仅有的几位文化课教师,从不奢望在西山武校“指点江山”,只希望在这比自己家乡富庶的东南沿海多挣个三十五十,已补“少米之炊”。至于在学校里是“学”为主,还是以“武”当头,这都无关紧要。哪怕天天围着教练喊大哥也无妨。
就说说陈美桥吧,这位来自湖北黄梅县蔡山镇张王桂村的中师毕业生,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几年间,根本入不敷出,压根儿解决不了家里的贫困。都上世纪九十年代了,第一年的工资才56元,第二年也才71元,在农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,净指望他当上老师后,能有点出息,挣几个“铜板”回来养养家。可几十元的工资,究竟能养谁呢?
亏得有朋友帮忙引路,才背井离乡地来到福建,辗转了几个地方,才万分福气地来到西山武术学校。起先帮着贴广告,帮着学校搞搞接待,学校要给学生上文化课了,这才把他这个正规的师范毕业生抽出来教语文和数学课。由于教学出色,校长张文彬给他开了每月300元的工资,已经是家乡公立学校的四至五倍。每月能拿这么多工资,口袋里的钱一下子多了起来,月月都能拿一叠子钞票寄回家里。这样也算对得起父母家人了。